韩寒者,沪郊人也。身修七尺,貌俊神逸,性狂傲,不拘于俗。天朝三十四年,寒之诞时,天降异相,有善相人者言:必有文曲下界。众哂之妄言。寒果天资聪颖,三岁,识字千余,四岁能诵诗书。人奇之,曰:此子必成大器。其父闻之,欣欣然有喜色。
后之学馆,学百科知识。寒善属文,恶理算。然学制不可偏废,寒虽善文,亦独木难支,学业坎坷。年十七,学府举属文大赛,天下年青才俊,争相一试。寒以《管中窥人》,一举夺魁。年十八,著书《三重门》,一时洛阳纸贵,华夏震惊。或曰,此王勃神童再世。亦有人言:“无他,乃当世之仲永耳,后必泯然众人矣!” 寒闻之,誓曰:“汝今哂余,后汝等必悔之。”
寒身虽单,然善奔走,沪府举奔走大赛,令举,寒狂奔,众于后苦追,不及。寒独占鳌头,嘻曰:“此吾所长,吾尚未尽力。” 足见其有竞技之资。
后碍于算学,不能晋级,按制当与学弟复习之。寒羞,愤然曰,“此学制之弊,非吾之罪,吾不与也。” 慨然退学,寒师言曰:“寒乃异数,乃昙花耳,众不必效也!”
寒既退学,专心属文,著书立说,立论无数,声名大振。
五十五年,天朝兴赛车之戏,驾之,风驰电掣,如驾云腾雾,寒喜其激荡,动人心魄,与已性相合,遂与之。辄夺魁,与人角而获利。人曰:寒者,真乃竞技之体也。
天朝一代,民生多艰。初,毛氏专政,兴运动,除异己,启文革,毁文化,天下大乱,生灵涂炭。二十八年,毛氏崩,邓公执政,废毛氏之弊政,务生产,兴经济;开国门,引夷长技,民渐不为食忧。然变革止于经济,于政无改,特权之层,官商丨勾结,为一已之利,中饱私囊,变革之果,多为其所掠,民苦之。
天朝六十年,屋价高起,民以三代之资,尚无力购斗室居之;药价高起,一人得疾,辄倾全家之产,无力医之;学馆之费高起,下等之家,无力供子之学。贫富分化,民怨声载道。然权贵闭言路,拒忠谏,民有冤屈,无途诉之。偶有民负冤上丨访,寄望于青天,所属府吏阻之曰:“此非法也。” 辄捕之。京师大学堂有孙东东者,放言曰 “上丨访之民皆疯癫之徒。” 此言出,访丨民皆堵而抗之,东见激起民愤,大恐谢罪。
或曰:“官府有言,为民仆也,怎奈恶奴欺主乎?” 人对曰:“其为民仆?诳语耳,以欺民也,汝若以主居之,定和谐之。” 民勿敢言,噤若寒蝉。或有愚民念及毛氏,曰:“毛帝在日,吾等虽贫,然亦无富者,此公平也。” 寒既怜民苦,又怒其不觉,曰:“汝等无知,不知贫之根本,不公之源,乃专制之制,民不选官,官不畏民,遂酿此祸。如官为民选,民督其官,可也。观今之天下,一党丨执政之体,止存其八,多民不聊生。以此可见,此制民必贫,官必贪。救中华者,必以民丨主治国,优上劣下,方保民之利益。”
为启民智,寒遂于网间写博文,倡民丨主,批专制,疾恶如仇,文风泼辣,嬉笑怒骂,切中时弊。民甚喜之,皆曰:寒之语,道吾等心声耳。吾当力挺之。寒博观者如潮,名列华文榜首。国之少年,视寒为已之榜样,国之老者,视寒为国之未来。
然文联之御用文人,见寒势起,护主心切,群起攻之。白烨者,制内文人,善评者也,以正统自居,撰文批寒,寒回文讽之,你言我语,一时网间硝烟四起,新旧思想,一试高下,众皆挺韩,数合之后,烨见不能取胜,再论亦自取其辱,遂仓皇关博。
寒曰:“作协乃驯化之地,汝等皆阿谀奉承之辈,官府豢养之徒,专饰太平之辞,乃鹰犬耳。吾若主之,即刻散之。” 亦有文僚喉舌仇彦英,谈歌者,闻此语,老羞成怒,与寒博客论战,皆靡。
寒曾戏曰:“凡逻辑者盖二类,一曰逻辑,一曰中国逻辑。” 讽权贵指鹿为马,颠倒黑白也。
后西方之国,设一擂,天下精英,比其影响几何,票毕,寒名列榜首,国之重臣,王某、薄某皆名落孙山,举世哗然。以此见寒为天下人所爱,不谬也。
古语有之:防民之口,甚于防川,况世过时异,寒等有识之士,倡民主,启民智,民心已觉,人心思变,如若堵之,溃之速也。果抗争之事频发,有民妇唐福珍者,为保已产,引火自焚,慨然赴死,可歌可泣。类似之事,难以计数,民皆怒于心中,
……
天朝七十年,变,民主之制立,多党竞争,四年更替,皆民意决之。专制之祸永绝矣。人皆以寒功大,举寒主政,寒曰:“吾乃散漫之人,不宜入仕,吾之私爱,赛车红颜耳,汝等勿复再言。” 遂偕众友流连勾栏瓦肆,吟诗作赋,赛车玩犬,乐哉乐哉!
太史公曰:因材施教,夫子倡之,然时过二千余载,尚勿行,悲夫!寒虽不精算学,然文采斐然,当扬其长,避其短,然世之学制,务求其全,以绳梅、病梅为业,可乎!寒有专长,著书立说,声名大振,而时谓全才者,天下之多,何人成名耳,世人当慎思之。又寒文名虽显,然所以立于青史者,当为民请命耳。万马齐喑之时,寒与有识之士,为民呐喊,呼民主,斥专制。置身于险境而不顾,此等大义,吾当慷慨歌之,今世之大治,民畅所欲言,皆寒等先行者之功也,世人当念之勿忘,吾亦思忖良久,作传记之,以示后人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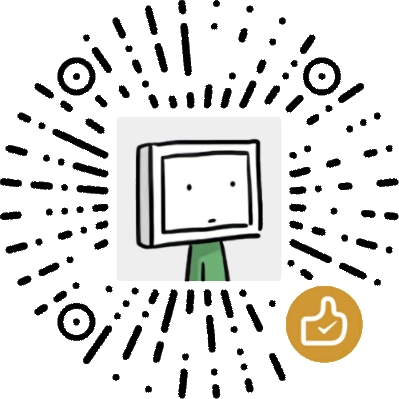

#cmt364
回复
#cmt363
回复
#cmt362
回复